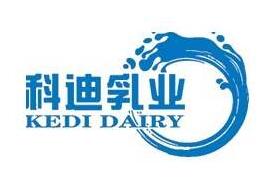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总则编,对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作出规定,在民法典中起统率性、纲领性作用。因此,民法总则草案初审,相当于本次民法典编纂走出第一步,草案分11章,包括基本原则、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民事权利、民事法律行为、代理、民事责任等。
民法典被称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本次民法典编纂,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次。改革开放后,曾两次启动民法典编纂,但因条件不成熟,均中途延期。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编纂民法典,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明确提出“编纂民法典”。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次民法典编纂随后启动。
6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表示,编纂民法典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民法典将由总则编和各分编(目前考虑分为合同编、物权编、侵权责任编、婚姻家庭编和继承编等)组成。总则编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和一般性规则,统领各分编;各分编在总则编的基础上对各项民事制度作具体可操作的规定。
李适时介绍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制定了民法通则、继承法、收养法、担保法、合同法、物权法、侵权责任法等一系列民事法律,修改了婚姻法,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近年来,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对编纂民法典的呼声比较高。编纂民法典已经具备了较好的主客观条件。
李适时表示,编纂民法典不是制定全新的民事法律,而是对现行分别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进行科学整理;也不是简单的法律汇编,法律汇编不对法律进行修改,而法典编纂不仅要去除重复的规定,删繁就简,还要对已经不适应现实情况的现行规定进行必要的修改完善。
本次民法典编纂,采用“两步走”思路:第一步,编纂民法典总则编(即民法总则),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后,争取提请2017年3月召开的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第二步,编纂民法典各分编,拟于2018年上半年整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分阶段审议后,争取于2020年3月将民法典各分编一并提请全国人大会议审议通过,从而形成统一的民法典。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近日梳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的意见,并采访了一些民法学学者。
六岁孩子或将有民事行为能力 这一步跨得是否大了些
“草案一下子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标准从十周岁下降为六周岁,我认为存在重大制度风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苏泽林表示。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规定,十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草案将此规定修改为,“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草案明确提出:不满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据了解,此前我国民法学界起草的多个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也基本采取了上述设计。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组织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就将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界限从十周岁降为六周岁。
李适时在作草案说明时表示,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是指自然人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行使民事权利和履行民事义务的资格。草案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年龄下限标准从“十周岁”降到“六周岁”,主要考虑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活教育水平的提高,未成年人生理心理的成熟程度和认知能力都有所提高,适当降低年龄有利于其从事与其年龄、智力相适应的民事活动,更好地尊重这一部分未成年人的自主意识,保护其合法权益。这一调整也与我国义务教育法关于年满六周岁的儿童须接受义务教育的规定相呼应,实践中易于掌握、执行。
苏泽林说,《民法通则》把十岁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起点是有道理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满十周岁的人,一般已经完成了初级小学的教育,进入了小学的高级教育阶段,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二是满十周岁的人单独接触社会的机会相对较多,有了一定的社会阅历,能够初步了解自己行为的一般性质和相对后果。从实践来看,这样规定符合我国实际情况。草案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年龄从十周岁降到六周岁,也就有可能让幼儿园的孩子承担一定的民事法律后果,这样规定不符合孩子的生理特征、不符合实际。
苏泽林建议维持现行民法通则的规定,如果一定要修改,建议降到八岁,六岁上小学,八岁上小学二年级,初步具备了一定知识,也有一定的社会阅历。
苏泽林委员的这一建议得到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列席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的赞同。何晔晖委员提出,考虑当前未成年人心理承受能力和认识能力有所提高,草案就把限制民事行为能力降到可以入学的六岁的法定年龄,“这一步是不是走得快了一点?建议下降到八岁,六岁小孩可能还没有走进校门”。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许振超也认为,从十周岁调整到六周岁的理由之一——“目前未成年人心理、生理成熟程度、认知能力有所提高”有些片面,“现在学校里、社会上六至十岁的孩子出问题确实比较多,但实际上是反证他们的心理、生理都不成熟,认知能力都不够”,他说,“要拿出足够的证据说明六周岁足够承担(一定民事行为能力),不能把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神童’的情况概括到全国。”
全国人大代表孙菁表示,我国不同地域、民族、教育环境下的六岁未成年人的认知和辨识能力是有差距的,定的年龄过低不利于保护未成年人,甚至为一些欺诈行为留下借口。
草案还规定,“十六周岁以上不满十八周岁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对此,许为钢委员认为,对十六岁至十八岁按收入判断是否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合适,按照草案目前的规定,一个人没有考上大学,去工作了,他有收入了,就要对自己的行为完全负责任了,但另外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应该是认知能力更强的人,他因没有收入就可以对他的行为不完全负责任。
孙菁表示,在校园暴力频发的当下,对此作出规定更应慎重。
监护制度调整引发诸多疑问
监护制度是保障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益、弥补其民事行为能力不足的法律制度。我国现行民法通则只规定了对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的监护。
草案对我国的监护制度作出调整,将被监护人范围扩大至智力障碍者以及因疾病等原因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辨识认知能力的成年人,将部分社会组织纳入监护人范围,并对撤销监护制度作出了具体规定。
草案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这就相当于扩大了被监护人的范围,除了未成年人、精神病人,智力障碍者以及因疾病等原因丧失或者部分丧失辨识认知能力的成年人,都在“被监护”范围内。
李适时表示,这一调整有利于保护智力障碍者等人群的人身财产权益,也有利于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好维护老年人权益。
201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曾两次召开座谈会,听取最高人民法院、民政部、国家卫计委、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残联、全国律协等部门,以及学者、律师对监护制度有关监护制度条款的意见。
与会人员普遍认为,过去《民法通则》把监护内容放在“公民”一章,是当时权宜之计,现在制定的民法总则对监护只宜作简略性的规定,监护的主要内容应该放在亲属法或者婚姻家庭法中进行规定。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老年福利处调研员陈建军认为,老年人的监护与其他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无质的差异,应统筹考虑。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指出,民法通则规定的撤销监护人条款,多年来是一个“沉睡的条款”。“没有人愿意提起诉讼并承担起监护责任,而政府的相关部门对此也不知所措,做多了怕越权,做少了怕出事。”佟丽华建议,在申请撤销监护权的主体中规定兜底条款,明确在没有人提起诉讼的情况下,民政部门要及时提起诉讼。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倪春霞赞同此观点。
在申请撤销监护权的主体方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维权部法规处副处长王治江表示,残联可以作为撤销监护权的申请主体。“特别是对于一些残疾人监护问题,残联介入的情况比较多”。
针对监护权撤销的情形之一“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行为”,北京国联律师事务所律师米良渝建议明确判断标准和调查主体。他说:“实践中经常发生夫妻双方在离婚期间,一方为争夺孩子的抚养权,擅自将孩子带离出境或者到其他陌生的环境,这算不算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草案规定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依法指定新监护人,并对提起撤销监护诉讼的主体、适用情形、监护人资格的恢复等作了明确规定。此外,草案还理顺了监护纠纷的解决程序,明确规定,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但一些学者对恢复监护权的规定并不支持。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梁慧星认为,设立监护资格恢复的制度风险很大,实践中“确有悔改”难以证明,且恢复监护资格会破坏已经形成的新的监护秩序。
佟丽华建议规定因性侵未成年人或者虐待未成年人致其重伤等严重情形而撤销监护权的,不能恢复其监护权。“一是对当事人及社会起到警示作用;二是撤销监护权后,未成年人可能通过民政部门找到收养家庭,确立新的家庭关系”。
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将“单位”纳入监护人的范畴,例如未成年人监护,如果其父母、亲属都无法担任监护人,那么其父母所在单位可担任监护人。草案删除了单位担任监护人的相关规定,提出“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可以担任监护人”。
对此,李适时表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单位与职工之间主要是劳动合同关系,而且就业人员流动越来越频繁,单位缺乏履行监护职责的意愿和能力。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公益事业的发展,有监护意愿和能力的社会组织增多,由这些组织担任监护人可以作为家庭监护的有益补充,也可以缓解国家监护的压力。
草案规定,“其他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的个人或者有关组织,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同意的”,可以担任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罗亮权提出,现在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职能弱化,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承担不了这个职责。
“有的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只有两三个人,哪有精力来管?建议由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同意、民政部门证明认可才行,建议这一条款要慎重研究,否则难以落实。”罗亮权说。
关于未成年人监护的问题,王刚委员表示,在现行的体制下,我国的未成年人绝大部分时间是在学校度过的。尤其是寄宿制学校,大部分时间都是学校在实际上做这些孩子包括人身安全等的管理监护。
王刚认为,学校这种管理属不属于监护,是否一种临时监护,这种监护权如何取得与赋予?建议在“监护”一节里面有一个适当的表示,更符合现在寄宿制学校长时间代替父母管理未成年人的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