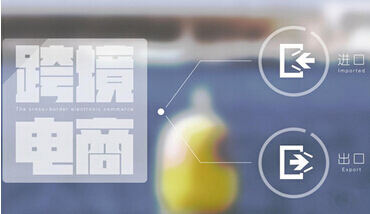我上一次看也已经是高一的事情了,所以剧情忘了大半。我在看的时候不免回忆一些剧情,“鉴定”这部片的主题是什么。友谊、爱和救赎已经是足够宏大的主题,但是对于这部电影稍显以偏概全。在玛丽和马克思的交流之外,他们也在走着自己的路,他们贯穿一生的充满裂缝(“full of cracks”)的路。

以孩童的视角看世界,悲惨的部分会蒙上懵懂和天真的色彩,从而削弱灰色的底色。玛丽的父亲,贫穷,寡言,孤僻,不愿意陪伴孩子,躲在车库里与死鸟做的标本为伴;玛丽的母亲,酗酒,偷盗,粗俗,浑浑噩噩。年幼的玛丽得不到很好的照顾,更别说得到关爱。她的童年伴随着没有朋友和校园暴力(虽然后来在马克思的指导下化解了);她的青春期伴随着热烈痛苦的单恋(虽然这在本片中只占很少的篇幅),和自觉丑陋带来的自卑。她的父母相继离去,以至于她的婚礼上,玛丽家只剩下玛丽一个人。
她也有幸运的时刻,她年纪轻轻在学术上取得巨大成功,何况这样的成功某种意义上还和自己的朋友马克思联系在一起,她追求到了青春期渴望的爱情,拥有了短暂的婚姻生活。随之,她的幸运急转直下。她的著作称她好朋友的症状为“病”,加以研究,大获成功,这激怒了马克思,因为这位她唯一的朋友说过,他不认为“阿斯伯格”是一种病。她陷入自我否定,多年疗愈积攒的勇气和丈夫相继离去。她走上母亲的老路,酗酒,不修边幅,四肢颤抖,或者说浑浑噩噩。吞下一大把母亲遗留下来的安眠药,站在悬挂在横梁上的绳索前,玛丽在“世事无常”的歌声中回顾了自己一生仅有的几个情感来源,逝去的父母,离去的丈夫,失去的朋友马克思。

马克思某种意义上也是个儿童,他以自己的方式解释着遇到的不公和恶意,奇特的解读中充斥着马克思的疑惑。奇怪的思路淡化了他生活悲惨的底色。童年时因为是犹太人被施以暴力,就像玛丽小时候因为额头上的胎记被嘲笑;仅仅因为参加了科幻小说爱好者协会被军队辞退。他有暴食症,抑郁症,阿斯伯格症,他紧张、易怒、无法与人交流,这几乎令他无法在成人的世界活下来,在中大乐透之前靠低廉的临时工资活着,住在破旧公寓的顶层,每周日得到一位近盲老太太的照顾。他认为人无完人,自己的特点并不是病,人们应该学会接受自己的裂缝(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最后原谅了玛丽)。他有一个幻想的朋友,但他的终极目标是拥有一个看得见的朋友(“not unvisible”)。在44岁的一天,他收到了澳大利亚乡村一位小女孩玛丽的来信。

在看到玛丽因为马克思的愤怒而把自己写的书销毁时,我在想,玛丽就不能断绝和马克思的来往,继续享受优渥的生活和已有的声望吗。这几乎不可能。马克思是玛丽一生中少有的爱的来源,在玛丽看来那本著作也是为了马克思所作,她把著作当作了礼物送给马克思。在她的生命中,爱的资源如此匮乏,当她自己辜负了自己拥有的爱,她在自己眼中就成了罪人。我联想到上周六看的电影《血观音》,这部电影也自称谈爱。但是《血观音》里逐爱的过程太黑暗了,是密不透风的隧道,布满了刀刃,没有一丝光亮,走进来的人只能走向更深的黑暗,更密的刀刃,那还谈个屁的爱。《玛丽与马克思》谈爱,它让人走在荒原上,荒原会天阴天晴,荒原会枯木逢春,荒原会有小径的交汇;有的路平坦有的崎岖,但起码能走,而且视野开阔。
最后玛丽终于来到了马克思的住所,兑现了将近二十年前的承诺,只是她稍晚了一步。马克思坐在沙发中,安详地微笑,抬头望着天花板,那里贴满了玛丽寄来的信纸和照片,见证这段跨越二十年的友谊。

这一刻,两个原本孤独的灵魂的相互救赎结束,中途有不甘和撕扯,有误伤和空间之隔带来的等待和折磨,马克思结束了人间旅途,玛丽也真正拥有了自爱的勇气。
这部电影还有一个在二战中因为日本人的残害失去双腿的坐轮椅的老头(我真的很难记住西方人的名字),历时45年终于克服外界恐惧症,不仅完成了自己的“救赎”,还救回玛丽一命(让她笑裂(bushi))。在我看来这个老头才是本片的最大赢家。另外两个戏份很重的角色,玛丽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堕落,影片没有交代(可能玛丽的父亲不算堕落,只是真的很丧和低欲望而已),他们最终都没能在死亡之前找回荒原上游离的自己,他们游离着抚养小玛丽长大成人,然后好像迫不及待一样相继离开了人世。
还有电影对于各种死亡戏剧性的、玩笑式的处理。我想起《恶童日记》,虽然画风完全不相同。过于密集的死亡和别离本应然观众对悲情产生抗体,但是真正着重刻画的死展现的时候,观众还是会泪目(指我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