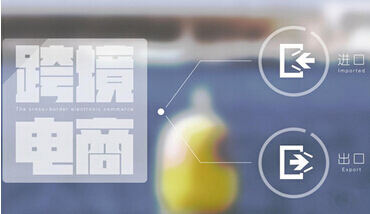2021年3月1日,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2020版《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显示,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轻度抑郁检出率为17.2%,高出2009年0.4个百分点;重度抑郁为7.4%,与2009年保持一致;其中,女生抑郁高于男生,非独生子女高于独生子女。
有机构曾对中小学校园中做过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年级增长,抑郁检出率呈现上升趋势。小学阶段抑郁检出率为一成左右,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约为1.9%-3.3%,初中阶段抑郁检出率约为三成,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6%-8.6%。高中阶段抑郁检出率更高些,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10.9%-12.5%。
抑郁从何而来?南京脑科医院儿童心理卫生研究中心医生王佳佳表示,青少年有如此高的抑郁率确实 “触目惊心”。她表示,青少年大脑发育并未成熟,遇到各种问题的自控和反思功能也不完全,更容易偏向于一些极端的思考方式。“当然除了来自发育认知的因素,还有社会环境、文化、家庭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
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本该是孩子温暖的避风港,但很多时候家庭却成为压垮孩子的“最后一根稻草”。王佳佳告诉记者,家长最容易出现的一种误区就是把孩子的情绪当做“耍脾气”,是青春期逆反的正常现象。“青少年儿童的心理问题很多时候表现在行为上,如果家长能及时识别出信号,观察到孩子出现不同以往的行为问题,就应该给孩子更多的理解和支持,严重时及时就医。”
王佳佳也表示,其实大家不必对家长和亲子关系过分悲观。大部分家长的能力足够,只是对疾病的认识不足;孩子也还是信任家长的,出现问题会用不同的表现向家长求助。“关键问题是,家长怎么理解孩子发出的求助信号。”王佳佳举例,不少孩子语言能力好,会直接表达情绪,但有些孩子则是通过上学困难等行动表达。如果家长一直质疑孩子,总认为孩子的情绪是小事,或者问“你是不是装的”,这种不当的沟通方式,就会让孩子越来越往后退,最后就不愿意再表达,退缩到自己的世界里面。
王佳佳建议,家长首先要做的就是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多与孩子保持沟通。当然更为重要的是,保持情绪稳定。“很多家长承受不了来自社会的压力和焦虑,把焦虑直接转移给孩子,这非常不可取。作为成年人,要保持思考的能力,在孩子出现问题的时候要多思考。不要孩子哭,家长跟着哭得更大声。”
南京市儿童医院心理行为门诊黄懿钖观察到,近年来随着二胎、三胎政策的放开,儿童生活习惯和环境的改变,比如更少的户外活动时间,更多暴露于手机、电子产品等,隔代抚养等问题出现,儿童的心理行为问题的确会有低龄化的趋势。在学龄儿童、青春期儿童身上更为突出的学习困难问题,抑郁、焦虑等情绪障碍、适应障碍问题等。
黄懿钖分析,当前青少年心理危机爆发集中在家庭场景,多源于亲子矛盾激化,包括家庭关系不和谐、家庭矛盾冲突、家庭教养方式的不一致等问题,中小学生报告其家庭功能重度不良的高达21%。所以青春期孩子的家长要充分了解这个时期孩子的心理特点,改变养育方式,如果有明显的亲子冲突和家庭不和谐的问题,或者察觉到孩子有难以调整的情绪问题,要带孩子尽早到心理专职机构就诊咨询。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南京神康心理医院心理科主任马珂主告诉记者:青少年心理危机只是多种学生心理问题的最严重表现形式。心理危机早期预防的关键问题是透过危机的表征找出高危群体,然后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才能进行有效的预防和干预。要做好危机干预工作,首先要做好学校的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如定期对学生进行心理测评、建立心理健康档案、对家长进行心理健康科普知识讲座、在学生中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等;其次,对任课教师进行心理问题识别和转诊技能培训、在学校中配齐专职兼职心理老师,并对心理老师进行持续培训和督导;最后,和校外的专业心理卫生机构建立联系,对高危的孩子及时转诊,接受专业治疗。
保护青少年儿童心理健康还有多远的路要走?需要涉及教育、卫健、民政、共青团、妇联等多个部门协同努力,不能因职能划分不清、职责交叉等问题,导致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谁都管又谁都不管”。黄懿钖建议,作为儿童青少年精神卫生工作者可以主动进入学校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心理危机识别与处理工作,参与构建以学校为责任主体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干预机制,形成“学校-医疗-家庭-社区”四级干预队伍。
青少年心理健康养成需要社会齐发力,要正确认识学校、家庭、社会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中扮演不同角色的重要性。马珂表示:“每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通常有个有问题的家庭。孩子的心理问题一要及早重视,此外,要多从家庭、家长身上找病因。”马珂认为,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家长对孩子的关注有加,而严格要求不足,一家老少几代人围绕着一个宝贝转,导致孩子以自我为中心,缺乏约束意识、规则意识。孩子心理健康成长,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关注。